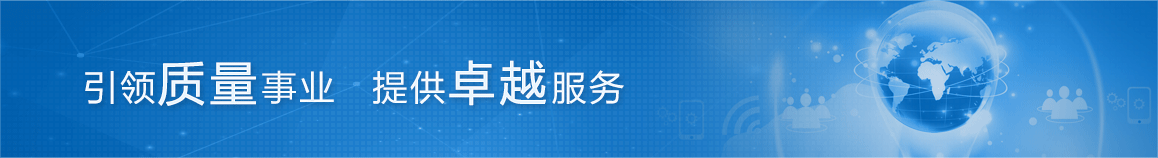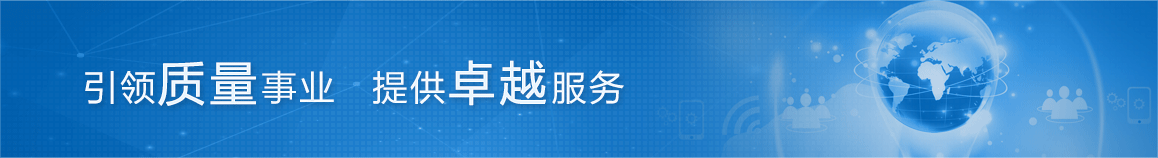李格尔(Alois Riegl)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主要代表,现代西方艺术史的奠基人之一。在视觉主义占据艺术主导地位的欧洲19世纪,李格尔借鉴经验主义哲学家们所研究的“触觉”艺术形态,将“触觉”概念引入艺术史研究当中,打破了视觉艺术统领一切原有的艺术史研究的格局。本文尝试从李格尔的触觉-视觉图式的起源来考察李格尔提出触觉-视觉图式的研究目的、策略、来源及环境影响。
李格尔的触觉-视觉图式研究的根本目的,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触觉-视觉图式”概念来提升艺术的地位,尤其是工艺美术的地位,因为19世纪时期的绘画艺术,其社会地位相对于文艺复兴前已经提高很多,艺术家已经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名字附在绘画作品上,而工艺美术却因内平面性和无表述性的地位,从属于绘画这一大的门类而被人轻视。李格尔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可以说都是为当时为人们所轻视的工艺美术和装饰纹样正名。他于1881年被吸收为维也纳历史研究所成员,1889年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期间课程开设的内容就是纹样史。在此基础上,李格尔开始撰写《风格问题》,并且成为研究装饰设计最杰出的著作,而《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被则称为西方美术史的经典之作,但研究的主体还是工艺美术或具有装饰性质的早期基础绘画。李格尔正是通过早期基础绘画的“工艺性”、“装饰性”将工艺美术与绘画等同起来,以此来为工艺美术和装饰纹样正名。
在经过15世纪的文艺复兴、17-18世纪的巴洛克艺术、18世纪的洛可可艺术、18世纪古典主义绘画、19世纪初的新古典主义、19世纪中叶的浪漫主义绘画等各种风格流派的发展演化,在西方绘画透视学、现代光学等现代科学的影响下,再现性绘画在技法表现上已经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顶峰,让人为之沉迷。绘画艺术的社会地位,在众多艺术家、艺术理论批评家的努力下,在学科地位上已经与人文学科并肩而立,而这些西方近现代绘画的历史根源,可以说都是源于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和绘画艺术。因此,李格尔通过对最具写实性的古希腊艺术进行了一个历史时代地位的划分,从而把其所在的19世纪的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纳入李格尔为艺术等级设立的艺术金字塔的中间段。而工艺艺术和装饰相对于绘画来说,由于其表现性、视觉性和内容性,与再现性绘画不可相提并。所以,把工艺美术和装饰纹样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李格尔,在其艺术理论中,实际试图通过触觉-视觉图式概念,把工艺美术放在再现性绘画的等级之上,来尝试证明工艺美术和装饰纹样并不是简单、低级的、没有思想的工匠作品,而是蕴含着人们知觉形式最高目标的艺术品,处于艺术金字塔的最顶巅。而罗马晚期、早期基督教的绘画及纹样,因其形式上更接近于工艺美术的效果。因而,李格尔通过触觉-视觉图式理论,自然地把绘画艺术变成了工艺术美术高高在上的立足点。
李格尔通过触觉-视觉图式远近距离的不同来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埃及艺术、古希腊艺术和罗马晚期的艺术特征变化,把“艺术意志”的唯心理论作为艺术发展不可否决、不容置疑的内在动力,来说明工艺美术和装饰纹样必然是人类心灵的最高形式。在这种结论下工艺美术的简洁、节奏、抽象的造型性特点是心灵知觉的最高表现,工艺美术和装饰纹样是精神寄托的最高境界。
李格尔认为古埃及的艺术,是近距离的触觉艺术。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类还处于最原始状态,人们并没有空间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混沌的一片的,所以,只能通过触觉的方式,才能感受到单个物体的关系,也只有触觉才能切实感受到“物的不可入性”,了解单个物体的实体状态,物体与物体之间是没有空间的。这也是古埃及艺术如金字塔在硕大的空间里,没有空间的原因,所以此时期的艺术是表面触觉性质的。
到古希腊时期的艺术,尤其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以瓶画为主,人类的视觉功能已经在起作用,在触觉-视觉图式的正常距离下,这个视觉实际上指的是“视觉对象”在心灵上投射出的集合表象的一种形式。 人们会注意到如细节的美、衣物、造型的美,按照李格尔的理解,这些集合表象,不是由生理学意义上的“视觉对象”、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知觉表象”形成的,即在心灵知觉下,感受到视觉对象产生的“视觉投影”(希尔德布兰德),而这个视觉投影则寄托着灵魂,这个知觉表象的形成,是不能单靠触觉完成的,而是需要通过“空间”,即一个适合的距离,才能把各个物象的点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知觉的表象,在这个知觉表象里,寄居着灵魂。
李格尔的正常距离的触觉-视觉图像,表明古希腊那些写实性在当时包括现在看来依然优美的雕塑很写实逼真,是触觉和视觉指导下的艺术作品。这个结论从另一个方面,也暗示着19世纪李格尔自身所处的绘画艺术环境,尤其是写实性再现性绘画,不过是人类心灵“艺术意志”的视觉-触觉图式的过度阶段,从而从侧面肯定了工艺美术的崇高地位。而远距离的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也包括这时期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基本完全处于知觉表象的形式阶段。这个阶段的艺术形式,在李格尔的观点当中,这才是心灵精神寄托的形式,因为,这种图像已经摆脱了触觉最混沌的时期的艺术特点,而留下了视觉的最高形式。从而再次说明罗马晚期的艺术,包括工艺美术在内,已经完全摆脱了诗歌、文学、宗教的内容,形成单纯视觉的崇高地位,它关于客体物质不可入性的经验不是那么直接,而是基于触感的联想。
李格尔的触觉和视觉其实与人类的空间关系的发展,从艺术外可以追溯到欧几里德空间几何。在欧氏的平行公设的作用下,欧氏几何中的空间生成过程,首先设想一个点,将它向任意方向上移动一段距离,它的轨迹就连了一条“线”。然后将这条线段向其他任意方向移动一段距离,它就变连成了一个“面”。然后将这个面向其他任意方向移动一段距离,它的轨迹就连成了一个“体”。这取决于我们所需容纳对象的多少,将这个“体”在刚才的三个方向上等比例放大或缩小,也就形成了笼括我们日常生活各种事物的那个“空间”。这样,通过点的方式和连线的方式,形成了一个面。格尔触觉-视觉概念中的视觉概念,很类似于从欧氏几何,把物体的各个点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视觉投影”平面形式,而绘画艺术正是这样的一个艺术。
李格尔视觉形式的平面感,则是始于希尔德布兰德的“视觉投影”。希尔德布兰德认为,形式的观念并非来自事物的本身,而是来自艺术家这一事物整体的不同视点的比较中概括出来的某个视面。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对从不同视点所观察到的诸视面进行比较,在繁多的材料中选择并表现最能展示他形式概念的因素[i]。在这里,视知觉是空间知觉的精致分析,同时也是形式理论的基础。立足点是在平面,以平面来统一空间[ii],当一个物体距我们一定的距离之外,我们的双眼便平行地观看它,从而获得一幅单纯的,二维的画面。“尽管人像实际上是一个实体,但只有当它取得平面图画的效果时,才获得了艺术的形式,就是说获得了我们视觉的完善。”
在罗可可艺术兴盛的时刻,同时也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盛兴的时代,绘画的再现性影响人情感的功能,瓦萨里的《名人传》已经为绘画艺术地位树碑立传,鲍姆嘉通基本确立了美学的学科属性,而康德则通过知、情、意,为美学规定了范围,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内容,所有这些研究,基本都是从绘画方面来阐述的。而工艺美术的研究则基本处于一片空白,工艺美术和装饰纹样的制作者被列于一种工匠的地位,相对于绘画地位来说,要低得多。再者,照相术的诞生(1826年1839年8月19 日,法国画家达盖尔公布了他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于是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可携式木箱照相机),使再现性绘画艺术受到强烈冲击。使自文艺复兴以来,在透视学和光学指导下的绘画艺术,加上17世纪的荷兰画家维米尔已经使用了类似照相术的暗箱技术原理[iii],使绘画艺术在整个西方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在在照相术的冲击下,使绘画艺术面临着跌下神坛的危机。而这种危机,甚至可能使艺术这一崇高的精神创作活动包括工艺美术会归于沉寂,这是艺术家们不能想象的,更是工艺美术研究者难以接受的。
李格尔的视触觉与距离的关系,也影响着后人的空间观和绘画创作观,如沃尔夫林的学生吉迪恩把建筑史纳人到各种空间的概念化体系中,把人类的建造历史划分为三个前后并列的建筑空间概念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如美索布达米亚人和埃及人的金字塔,这时的人们在思考着怎样去建造,不过暂时只是从外部出发,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建筑室内空间;第二阶段:建筑室内空间得到了表达,而建筑外部却被忽略;第三个空间概念,1929年,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的德国馆,使几千年的外部与室内空间的分离状态被一笔勾销。空间从封闭的墙体中解放出来,创造出室内空间之间,以及室内空间与外部空间之间自由流动、穿插和融合,产生出现代建筑的“流动空间”。[iv]
李格尔强调了触觉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是对黑格尔对触觉重要必轻视的纠正,黑格尔为在《美学》中他坚定地说:“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v]黑格尔的艺术史观点使得艺术史的研究一度倾向于从艺术家的“绝对精神”的角度探求以视觉艺术为主的艺术发展史。然而,李格尔借鉴经验主义哲学家们所研究的“触觉”艺术形态,将“触觉”概念引入艺术。
李格尔的现代知觉观念,在20世纪初摄像术出现的情况下,为绘画艺术的转型,提供了理论武器。此后,再现性写实不再是绘画艺术唯一表现手段,开始以艺术家个人个性为特点的现代艺术主义绘画。李格尔说:“这样一种艺术,离开了自然的、为人普遍接受的触觉物质性的领域,……它依靠理解力,即观者的主观激动。这种艺术不再考虑即便在那时所有受教育的人中的一般欣赏水平”,从感官的特性方面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以来的艺术会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观念化,其意义常常不是直接显现于作品的感性形式,而必须结合某些观念才能得到理解。(刘龙真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副教授)